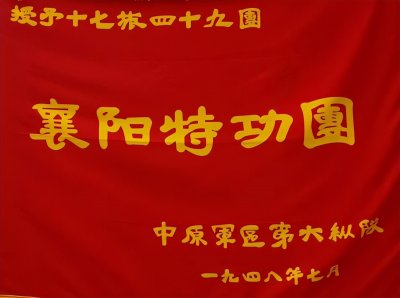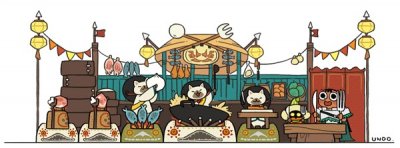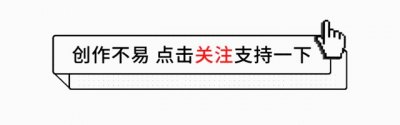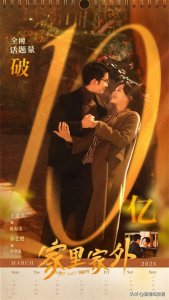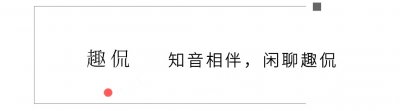功利主义学说批判

人应该以什么作为一生的追求和宗旨呢?
是应该按照内心的准则去生活,这样的生活才算高尚,才算超迈。哪怕焦头烂额,哪怕被嘲笑迂腐也要在所不辞?
还是应该以现实的利益得失为转移,这样的生活才算理性,才算务实。哪怕变得市侩、庸俗也至少乐在其中?
有趣的是,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大都提倡前者;而世俗之人却多选择后者。理论世界和现实世界巨大的鸿沟可见一斑。有没有一种学说能够解释现实选择背后的合理性?即如果我们抛弃道学家们苦口婆心但不切实际的教导,如果大家都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让所谓的道德去见鬼,我们真的会变成鬼吗?
兴起于18世纪的近代功利主义学说给我们做了一次有趣的理论推演。

抛开古代的理论源头不谈,近代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边沁和穆勒,其中穆勒所著的《功利主义》恰是功利主义最集中、最全面的表达。我们可以以此为蓝本了解这一学说,看看一个世俗到底的世界是否可能。
首先,穆勒认为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和抉择都有一个根本倾向,那就是快乐(或称作“幸福”)。
“快乐与摆脱痛苦是值得追求的两大人生目的,而所有值得追求的东西之所以值得追求,要么是因为它们本身含有内在的快乐,要么就是因为它们属于增进快乐和防范痛苦的手段。”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
虽然对于每个人来讲,代表幸福的事情不一样,但这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个认知问题,每个人都倾向于做他认为对自己最有好处的事情。

功利主义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应该是最容易理解也最能引发同感的伦理学说?但难点不在于对它的理解,而在于对它的质疑。它以极端世俗的态度回答了一个极端根本的问题。这引起理论世界的强烈不满,一直以来遭受到批判和攻击。
攻击一:怎么证明人的根本倾向是追求幸福?
首先,没有人能给“幸福”或“快乐”给出客观的、外在的定义,这是一个纯主观并且是最原始的感受。所以谁也无法证明“我们为什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幸福?”。
其次,我们还无法回答“为什么某件东西能使我们感到幸福?”因为有很多我们追求的东西,其本身只是身外之物,但他却能让我们产生幸福感,所以我们才追求它,它看上去是目标,实则只是手段,最根本的还是幸福感。但因为我们说不清什么是幸福,所以我们也无法获知“为什么有些东西能够让我们幸福?”。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绕,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终极动机的问题,终极动机是一切行为的主观原因,它是用来解释行为和抉择的,它本身当然无法被解释和说明。

攻击二:功利主义只知道享乐,太肤浅了。
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消解大众对“功利”一词的误会。穆勒强调一定要把“功利主义”中的功利和日常生活中的“功利心”中的“功利”区别开来。
很多人认为功利是肤浅的、自私的感官享受,把功利主义等同于享乐主义。其实虽然功利主义强调“快乐”,但快乐并不是只指没心没肺的感官享受,精神的愉悦也算作快乐的一种,所以功利是可以很深刻的。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功利意味着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算计,一种想占尽便宜的斤斤计较,如此一来功利反而是不快乐,它只能引发患得患失的焦虑——这也不对。功利指的是“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因为一些蝇头微利而牺牲了快乐,这恰恰是不“功利”的。
由此可以看出,功利主义强调的快乐包括了从精神到感官的多种层次,如果两个快乐发生了对冲,那么最终得到的快乐是一个减法结果,并不是快乐的最大化。

攻击三:如果多种快乐之间不得不发生对冲,应该怎么抉择?
穆勒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专门对快乐做了“质”和“量”上的区别。量的区别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就是愉悦的程度。而质的区别就是精神快乐和肉体快乐之分,他并且认为前者在“质”上碾压后者。这里会有人问,虽然道理都懂,而且按照穆勒所说人都会选择快乐最大化。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在可以享受高雅的时候却仍然忍不住投入感官愉悦的怀抱,然后在事后懊悔不已?
穆勒的解释是这样的:高级快乐虽然能给我们带来高级的精神享受,但要真的能充分享受其中的奥妙还是需要门槛的,穆勒将其总结为三个条件:高品位、有闲、有钱。
攻击四:如果自己的快乐与别人的快乐发生了对冲,该怎么办?
这或许是人们对功利主义最大的误解,认为功利主义就是自私自利,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程度的幸福,“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为了妥善协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穆勒提出了“最大幸福原则”:功利主义所追求的利益并不是行为者个人的利益,而应该是全体总利益!
这实际上是将功利的主体泛化,将个别的主体镶嵌到整体的主体中去,既然个体从属于整体,那么个体功利也应该服从整体功利,有了这个概念上的拓展,不仅自私自利的理论困境迎刃而解,而且功利主义的格局一下子打开,成就了牺牲自我、奉献社会的高尚境界。

总之,通过一系列的申辩,功利一词完全从日常语言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可以在理性层面上说得通的、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概念。作为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说不再是庸俗的、自私的、冰冷的算计,而是一个充满牺牲精神、兼顾精神境界的伦理学说。
这个伦理学说不仅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人类“逐利”的本性,而且也能够将克制、牺牲的伟大精神收纳进来,做到了自我和他者、个体与群体、肉体与精神各方面需求的统一。无论是面对在世俗生活中挣扎的普罗大众,还是侃侃而谈的学者大儒,似乎都无懈可击。
但也只是“似乎”,下面我试着谈一谈功利主义的迷雾:
《功利主义》一书写于19世纪的英国,约翰·穆勒家学深厚,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和自然科学精神的濡染,带有很浓的现代实证精神,实证观念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可以观察和测量的,进而也是可研究的。
功利主义完全可以看做实证主义在伦理学中的扩展。不管是追求“个人幸福”还是“最大幸福”、也不管这二者之间是何关系,功利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快乐和痛苦是可以量化并可以做加减法的。功利主义的迷雾的源头几乎全都来源于此。

首先,幸福概念的模糊性。
快乐和痛苦真的可以量化吗?或者真的可以在做抉择之前量化吗?任何事情只要一牵扯到人,就马上变得异常复杂和抽象。只有客观的东西才可以量化,因为它们只能被动地受外在规律和力量的左右,既然这些规律和力量是外在的,那就是可自外观察甚至控制的。但人有主观能动性,这个能动性是流动的、自由的,它可以随机组合、筛选外在影响。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看待人的行为,你会发现它毫无规律可言,原因很简单——他是人,不是物。
我们对外界的主观感受化作情绪在心底流动,毫无头绪并且转瞬即逝。有时候同样一件事情,情境稍微发生变化,就会在心底激起不一样的涟漪。我们小时候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长大之后再去做就变得索然无味;相反小时候不在意甚至反感的东西,长大后却深得其味。还有很多时候,在一些重大抉择之时,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样选会对未来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因此后悔,这个时候谁能有十足的把握说这样做更幸福呢?
当功利主义告诉我们“每个人倾其一生都在追求同一件东西——幸福”时,他说了一句极度正确的话,但实际上也是一句极度的废话。他看似点破了、总结了我们所有的追求和向往,但相对于生活中那些具体的、生动的道德选择,“幸福”二字只起到一种类似于集合的作用,它囊括了一切,但没有整合一切。
我们要的不是正确的废话,而是能指向根本的话。

其次,以行为结果(功利)为标准的不可操作性。
正如文前所说,关于所有伦理道德最终的依据,伦理学分为两大派别,一派认为应该按照心中的规则来做事;另一派认为应该按照现实的反馈来做事。
功利主义属于后者。在穆勒看来,道德原则太过教条,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没有可操作性,倒不如按照现实幸福这种显性的标准作依据。
但如果像刚才所说,功利主义认为现实幸福比道德准则更显性,是因为他觉得幸福是可测量的,而我们刚刚论证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没有办法在做每一件事之前去预估它给自己甚至全人类带来的利益(更不可能算出到底个人利益大一些还是群体利益大一些)相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明显感受到的是道德准则在心中形成潜移默化的行为模式,化作下意识的动作。
还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完全正确地预测行为的结果,所以如果以结果而非出发点去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实际上有失公允。
由此看来,无论是事后评价一个行为还是事前指导一个行为,以功利结果为依据都是不妥当的。一个既不能指导我们也不能评价我们的伦理学说不可能与现实接洽。
一个无法与现实接洽的学术,其生命是不可能旺盛的。

第三,以利益为标准的非道德性。
无论是“幸福”还是“快乐”,穆勒一直在逃避一个刺耳的词汇——“利益”。他就是想说人的行为应该以利益为转移,只不过这个利益的外延应该扩大到精神层面和群体层面。无论他怎样强调作为学术概念的“功利”与日常语言中的“功利”有何不同,他们二者的相通指出依然显而易见。
人可以以利益为转移来做选择吗?当然可以。
但你不觉得这应该是经济学的前提吗?
穆勒其实就是想打通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为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提供稳固的道德支撑,往大了说,他想为19世纪刚刚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提供道德合理性。
抛开这些背后的动机,我们就学术来讲学术,来谈谈经济学与伦理学到底可不可以融合。
经济学的任务是指导个人在市场浪潮中以最高的效率获取财富,或者指导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利用各种金融杠杆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它们对人性的设定只有一个“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学就是要利用这种“逐利”的天性来构建市场秩序。也就是说,市场逻辑的底层就是“要鼓励人性的贪婪,鼓动人们之间的竞争,甚至要鼓励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当然,这倾轧要保持在不会发生反抗的程度),只有这样市场才能持续繁荣,资本才能不断增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想要在“利”字之外再给自己标榜一个“道”(如中国古人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两个标准势必会冲突。
那么伦理学呢?
如果说经济学是放大人性,那么伦理学的任务就是要人去战胜人性;
如果说经济学是对利益的成全,那么伦理学是对利益的克服;
如果说经济学想要构建的市场是另一座人造丛林,奔走于其间的人类只是穿戴着衣冠的野兽,那么伦理学想要做的恰恰是在这群特殊野兽的身上刻上纹饰,以时刻提醒自己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物种更是一个自觉的物种。
所以,利益该如何放置在伦理之中呢?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