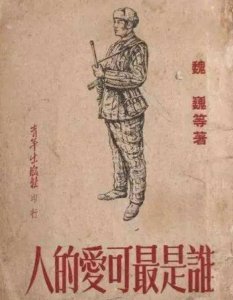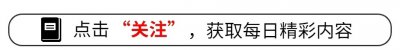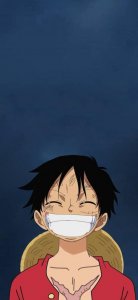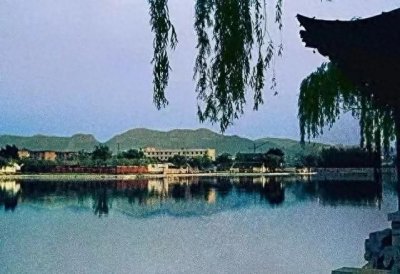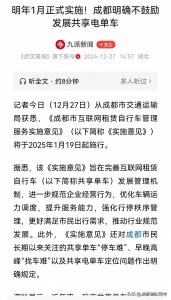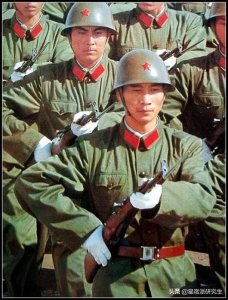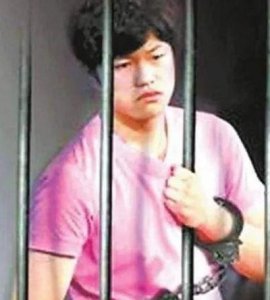马邑之谋:一场精心设计的围剿大戏,一个不得不杀的有罪之人
西汉在汉高祖刘邦创立后,又先后经过了刘盈、吕雉、刘恒、刘启,历时五代的不懈努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国策,国力大幅提升,在汉景帝刘启时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稳定了西汉的统治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个时候曾经秉承的与北方匈奴和亲的政策开始松动,汉武帝继位之后,也积极准备向北方这个强大的对手匈奴进攻,从而洗刷高祖刘邦白登之围的耻辱。

汉武帝需要一次尝试,对于匈奴他是陌生的,毕竟安逸的日子过得久了,汉武帝又是和从小就生长在深宫内庭的皇帝,他和自己的爷爷文帝刘恒不同,没有在代地和匈奴人的斗争经验。在他看来,匈奴人的问题应该可以通过军事行动,一次性的解决问题。
聂壹的主意:利用马邑诱惑单于来犯,而后集中兵力围而歼之。
历史给汉武帝提供了一次机会,地点在雁门郡马邑县,提出围剿匈奴人计划的是马邑县本地的豪强之士聂壹。
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资治通鉴·汉纪十》

他通过大行王恢,向汉武帝提议说:“匈奴最近得以与汉和亲结好,因而亲近信任边境的官员和百姓,可用钱财利益诱他们的前来,汉军预设伏兵袭击他们,这是肯定会打败匈奴人的一条妙计。”
上召问公卿。——《资治通鉴·汉纪十》
听王恢这一说,汉武帝有些心动,但他不想贸然行事,毕竟发动战争是一件大事,关联极大。而且对于匈奴人,大汉一直心有余悸,除了刘邦的白登之围,从没有真正意义上再次与其发生大规模战斗。
王韩之争:表面上是战与不战的问题,实际上是无为而治和进取有为的问题。
于是汉武帝召集公卿,讨论聂壹这个建议的可行性。这相当于是汉武帝主持,在朝堂上进行的一场辩论,事关大汉对匈奴的国策。

力主实行这一计划的大行王恢说:“我听说代国保有它的全境时,北面有强敌匈奴的威胁,对内还需防御中原诸侯的进攻,仍然可以尊养老人、抚育幼童,按照季节时令种粮植树,粮仓也一直有充足的储备粮食,匈奴人不敢贸然轻易的入侵。现在凭借陛下的神威,又有天下一统的优势,但匈奴人的入侵却持续不断,形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没有别的,就在于没有使匈奴人感受到汉朝的军威,我私下认为打击匈奴对国家有利,应该扬威于外,我们不用再忍受下去了。”

对于王恢的这种说法,韩安国并不赞同,他说道:“我听说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七昼夜没能吃上饭,等他解脱围困,返回都城之后,却没有复仇雪耻之心。圣明的君主应该有包容天下的气度,不应该因为自身的私仇而迫害天下的大公,所以高祖皇帝派遣刘敬为使者与匈奴人和亲,到现在已经为五代的人带来了益处,我私下认为不打匈奴对国家才算是有利,因为那会破坏管家安定的局面,为天下百姓带来灾祸。”
王恢反对韩安国的话,他说道:“您说的不对,高祖皇帝当年身披铠甲,手持利器,征战将近几十年,他不向匈奴报复被困平城的怨恨,并不是因为力所不及,而是出于让天下人休养生息的仁德之心。现在边境经常受到匈奴人的侵扰,受伤战死的士兵也很多,中原地区运载阵亡士兵的棺木车辆络绎不绝,这是仁德的君主所悲痛的事情,所以打匈奴是理所当然,国内群情激奋,对于打击匈奴也会责无旁贷倾其所有。”

韩安国对于王恢的慷慨激昂并不感冒,他继续说:“你说的不对,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总是让自己的军队以温饱等待敌人的饥饿,严明军纪等待敌人的混乱,安居军营而等待敌人的疲劳。所以一旦交战就会全歼敌人,一旦进攻敌国,就会攻破敌人的城防,经常可以安坐不动就能迫使敌人俯首听命,这是圣明君主的军队。现在如果轻易的对匈奴人用兵,长驱直入难以成功,如果孤军深入就会受到威胁,如果齐头并进就会后继乏力,如果进军太快,就会缺乏粮食供给,如果进军缓慢,就会丧失有力的战机,军队还没有走出一千里,就会人马都缺乏粮食。所以兵法上才会说:‘派出军队,就会被敌人擒获’,所以我说不打匈奴为好。”
王恢说:“您说的不对,我现在所说的打匈奴的方法,本来就不是征发军队去深入敌境,而是将利用单于的贪欲之心,引诱敌人进攻我们的边境。我们挑选骁勇的骑兵和冲锋陷阵的壮士,暗中埋伏,用来防备敌军,谨慎的据守险要的地势,以加强防御的力量,我们的部署已经完成,有的军队攻打敌人左翼,有的军队攻打敌人右翼,有的军队阻止敌人前进,有的军队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这样就能擒获单于,必定大获全胜。”

王恢和韩安国讨论的实际上是两种国策,韩安国主张按照高祖刘邦所制定的和亲政策和匈奴之间保持和睦关系,以继续推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发展大汉的生产。而王恢则主张积极进取、主动出击,扭转大汉对匈奴的颓势。一个是守成,一个是进取,本就没有对错之分,实际上是大汉国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汉武帝是裁判员,他选择做出改变,他要改变西汉建国以来的守成之策,而采取积极进取的对外扩张政策,同时他要洗刷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的耻辱,重塑大汉的强国地位,一战而令匈奴人战栗。
功败垂成:充分的战前准备,却败在了临战的细节上,一个卫尉的背叛,令几十万大军徒劳无功。
发动战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所谓谋定而后动,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才有可能去期望得到最好的结果。
首先就是要做好分工,安排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夏季,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统帅战车、骑兵、步兵共三十多万人暗中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约定等单于进入马邑城中就挥军出击。
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史记·匈奴列传》

汉军暗地派聂壹当间谍,他逃到匈奴人那里,聂壹对单于说:“我能杀死马邑县的县令和县丞,献出城池作为归降的见面礼,您可以得到全城的所有财物。”单于很器重和信任聂壹,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计划。聂政回到马邑县后,就杀死了几个死刑囚犯,用来冒充官吏,把他的头挂到马邑城上,让单于的使者观看,以此作为物证并说:“马邑的长官都已经死了,你们可以赶快来!”
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史记·匈奴列传》
这时单于越过边塞,统帅十万骑兵进入武州塞,走到距离马邑县城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单于看到牲畜遍布野外,却看不见一个放牧的人。
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史记·匈奴列传》

单于感到很可疑,就派人攻打一个亭,俘虏了雁门郡的尉史,并对这个尉史严刑拷问,尉史就把汉军埋伏的地点告诉了单于,单于听后大吃一惊,他说:“我本来就怀疑其中有诈。”就领兵撤退,在撤出大汉的边境之后,单于说:“我俘虏了这个尉史,真是天意保佑我呀!”
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史记·匈奴列传》

边塞的守军报告单于已经率军退走,汉军追到边塞估计无法追得上,就全军撤退了。王恢指挥的另一支军队,从代国出发,准备袭击匈奴残余的后勤部队,听说单于的部队已经返回了边塞之外,王恢畏惧匈奴人兵多势大,因此不敢出击。
有罪之人:马邑之围的失败,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如果不是王恢,就得汉武帝自己来谢罪。
汉武帝恼怒王恢不战而退,王恢为了保命对汉武帝解释说:“根据原来的计划约定,要匈奴进入马邑县城后,主力军队与单于交战,然后我率领军队袭击他们的后勤给养可以获胜。现在单于未进去马邑就全军撤回塞外,我只有三万人的军队,无法与拥有大军的单于交战,那样做只能是丧师辱国,我自然知道撤兵回来是要杀头的,但这样做却可以保全陛下的三万将士。”汉武帝冷笑了一声并不作答,把王恢交廷尉审判。廷尉判决王恢“避敌观望,不敢出击,判处斩首。”

王恢暗中向丞相田蚡行贿一千金,求他替自己开脱罪名,田蚡不敢向汉武帝直接求情,就对王太后说:“王恢第一个提出了在马邑诱剿匈奴主力的计划,现在行动虽然失败,但杀了王恢就等于为匈奴人报仇,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怎么能如此做呢?”

汉武帝朝觐王太后的时候,王太后就把田蚡的话告诉了汉武帝,汉武帝说:“最先促成马邑之围的人确实是王恢,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调动天下几十万的人马,安排了这次军事行动,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况且即使捉不到单于,王恢如果率领他的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还可以获得大批战利品,就算战死也是为大汉争光,朝廷还可以借此安慰将士们的心,而事到如今,不杀王恢就无法向天下人交代!”

王太后知道有人要为此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负责,如果不杀王恢,那这个责任就要由汉武帝来承担,这对即位不久还没有建立工业的汉武帝来说极为不利,因此王太后就不再说什么了。汉武帝的话,很快就传到了王恢的耳朵里,王恢得知武帝的话之后,自知没办法脱罪,就选择了自杀。
从守成到进取:马邑之围后,西汉和匈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至此,马邑之围落下了帷幕,尽管没有达成战略目的,但是意味着大汉的国策发生了根本改变,在经历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阶段后,汉武帝对于匈奴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心改变,他要高举战斗的大旗,从守成但进取的目的十分明显。
自是之後,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史记·匈奴列传》

从此匈奴断绝了与汉的和亲,开始进攻大汉的要塞,常常入侵汉朝边境不可胜数。但是匈奴还愿意在边关交界处保持互相开放市场,因为他们喜爱大汉的财物,大汉也不关闭边境贸易市场,以投其所好。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