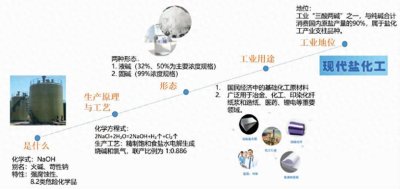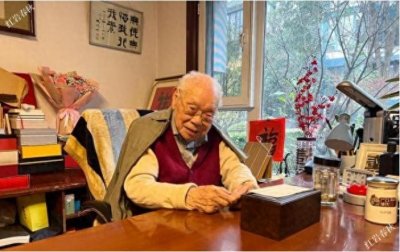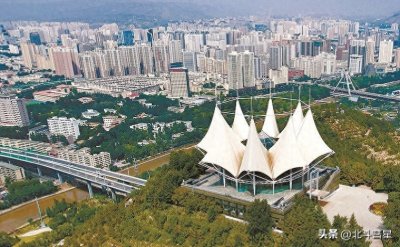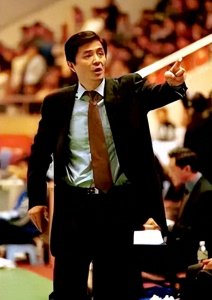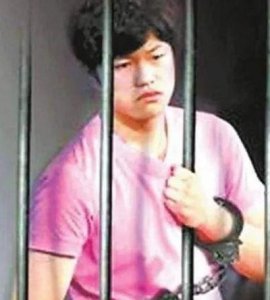官妓、军妓和野莺;2000多年的妓女制度如何撑起半部王朝治理史?
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国家妓院”出现在什么朝代吗?
你敢相信“官妓”、“军妓”制度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吗?
你以为古代文人墨客、士大夫的戴德水准真比现代人要高吗?
你敢相信忠心耿耿、威名显赫的岳家军也会征召军妓吗?
宋朝军队明令“不得私蓄营妓”,岳飞的部将王贵却因强征民女充妓被御史弹劾;更为讽刺的是,清朝《户部则例》禁止妓女购置田产,可苏州山塘街半条街的地契却是攥在几个名妓手中。

翻开《万历会计录》,一行小字记载着扬州盐商每年为官妓支付的“脂粉税”高达12万两,这笔钱足以建造三艘郑和宝船;敦煌文书P.3841号残卷里,沙州军妓每月要接待戍卒15次,每次仅值半斗黍米;在清代刑部档案中,北京胡同的暗娼接客一次的钱,只够买半个发霉的窝头。
这些令人吃惊的数据,揭开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妓女群体残酷的阶级分野:同样都是性产业从业者,有人变成了权力“白手套”,有些人却只能沦为如蝼蚁般的消耗品而已!
中国古代青楼女子作为特殊职业群体,其形成与发展贯穿2000余年封建史,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事实。各朝代对娼妓产业的规范管理呈现出的制度特征,以及从业者的等级划分与生存状态,折射出古代封建社会的阶层固化与性别压迫。

小编将从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官妓”制度演变脉络进行系统梳理,解析古代王朝不同等级妓女的生活。
一、官妓体系的形成与嬗变
1. 周代“女闾”制度的政治功能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创设的“女闾”制开创了官方管理性产业的先河。《战国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将战俘女性与罪犯家属充为官妓,既满足军队需求又增加财政收入。
“女闾”就是指妓院,“闾”表示房屋。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将七百个女性安排在这些房屋中从业,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妓女,也形成了“妓院”最初的雏形。
这种制度的设计,将性资源转化为国家治理工具,形成“以娼助政”的统治模式。

主要是齐桓公想要称霸,需要强大的国力和经济作为支撑。而由国家经营并收罗大量美女的妓院,不仅能吸引大量商人和贵族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还能吸引其他诸侯国的贵族来齐国消费,变相抢夺其他诸侯国的税收,从而增强齐国实力。
但是,这种妓院在当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纯粹以卖淫为目的的妓院,它还带有一定的文化交流和消息聚散功能。例如,其中可能有一些是间谍,还有的或是精神层面服务,不一定需要女子卖色,类似“卖艺不卖身”。
2. 汉代“乐府”体系的专业化发展
汉武帝时期设立乐府机构,将官妓纳入国家礼乐体系。《汉书·礼乐志》记载“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官妓需掌握歌舞器乐技能,承担宫廷宴会表演与外交接待职责。太初年间统计显示,长安官妓人数已达2000,形成专业化的艺术培训体系。

3. 唐代“教坊”制度的鼎盛形态
教坊作为中央直属的官妓管理机构,在开元年间达到鼎盛。《教坊记》详载长安右教坊“妓女五百人,皆特承恩宠”,按技艺分为坐部伎(器乐演奏)、立部伎(歌舞表演)、宜春院(高级艺妓)三个等级。教坊妓女需定期考核,技艺精湛者可获“内人”称号,享受从七品官员待遇。
唐代从七品官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干部。唐代的县令为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县丞为从八品,辅助县令管理县内事务,相当于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级别。
很显然,唐代教坊制度,有点类似于女性科举的上升渠道;琴棋书画成为官妓的必修课。
二、封建礼法下的等级体系
1. 官妓系统的三级架构
①宫廷艺妓:唐代宜春院妓女需通晓音律、诗文、书画;白居易《琵琶行》中“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即指此类。宋代崇宁年间设立大晟府,入选妓女须通过礼部考核,待遇等同九品官员。

②军营营妓:汉代“营妓”制度规定“卒妻女无家属者,补为军妓”,记录于《汉官旧仪》。意思是将士兵的妻子、女儿中没有家属的补充为军妓。
明代《大明律》确立“乐户”世袭制度,规定“娼优隶卒”后代不得脱籍,形成制度性压迫。所谓娼优隶卒,是指古代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四种职业人群。“娼”指的是娼妓;“优”指的是戏曲演员;“隶”指的是衙门里的差役;“卒”指的是士兵。
③地方官妓:元代《至元新格》设立“管领诸路娼妓总管府”,地方官妓需登记“乐籍”,每月向官府缴纳“脂粉钱”。明代南京旧院设有“富乐院”,妓女按才貌分为上厅行首、时官、私窠子三个等级。

2. 市妓群体的商业分化
①书寓妓女:清代上海租界书寓妓女需通过“弹词”考核,能说唱《珍珠塔》《玉蜻蜓》等长篇弹词者方有资格挂牌。此类妓女多通文墨,收费标准每局银元五枚。
②长三堂子:在晚清时期,上海的高级妓院实行“打茶围三元,出局三元”的收费标准。但妓女需要精通昆曲、京戏,能参与文人雅集。王韬《海陬冶游录》中记载,名妓李巧玲“每夕局票应接不暇”。
③野鸡妓女:底层流莺多聚集在城乡结合部,《清稗类钞》中描述她们“夜立街头,拉客过夜,资不过百文”。北京八大胡同处妓女需每日完成“卖铺”定额,否则就会遭受毒打。

三、职业妓女的生存智慧
1. 文化资本的积累路径
秦淮名妓柳如是在《湖上草》中展现出的诗文造诣,明朝大文豪钱谦益称赞其“清词丽句,不啻谢家夫人”。明代名妓马湘兰精于兰竹绘画,她的作品被收录入《石渠宝笈》,其艺术成就获得文化主流界名家认可。
这种文化修养,让高级妓女能够突破阶层壁垒,与文人士大夫阶层平等对话。
2. 社会关系的经营网络
宋代名妓李师师,她通过周邦彦成功结交了宋徽宗,《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其李师师的居所“金钱巷内,朱门绣户”。晚清时期的上海名妓胡宝玉,通过包养京剧名角杨月楼,成功跻身上流社会交际圈。
这种社交能力,能让妓女成为权力网络中的信息传送枢纽。
3. 经济独立的实现方式
唐代蜀中名妓薛涛创制“薛涛笺”,通过造纸作坊实现了财富自由。清代《扬州画舫录》中记载,名妓陈素素开设银号,资助贫困书生科考。
这种商业头脑,使部分妓女摆脱依附获得经济独立自主权和人格尊严。
四、制度性压迫与身份困境
1. 法律层面的身份禁锢
在《唐律疏议》规定“奴婢溅人,律比畜产”,妓女财产权被完全剥夺。明代《大明会典》确立“乐户世袭”制度,规定“娼妓所生子女,仍习乐艺”。

清代《户部则例》禁止妓女购置田产,其人身权利完全隶属于妓院。
2. 道德话语的双重标准
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批判“妓女之害甚于洪水”,却默许官员蓄养家妓。这种道德伪善加剧了妓女群体的污名化。清代青楼女子死后不得葬入祖坟,墓碑只能刻“待阙鸳鸯”字样。
3. 从良道路的制度性阻碍
宋代规定妓女从良需缴纳“脱籍钱”,数额高达千贯。明代《南京刑部志》中记载某妓女赎身需要支付“身价银二百两,另备妆奁”;这些制度将妓女永久禁锢在“贱籍”之中。
古代官妓与军妓的从业,具有鲜明的制度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贯穿于身份归属、服务对象、人身控制等各个环节,从而形成严密的压迫体系。

接下来从法律规制、管理体系、各种人身控制手段几个维度详细分析:
①世袭贱籍制度
唐代《户婚律》规定“乐户、官户、杂户皆为贱籍”,明代《大明律》更明确“娼优隶卒世世子孙不得脱籍”。
典型案例: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将战败的南朝刘宋宗室女眷“没入乐籍,永世为娼”记录于《魏书·刑罚志》。清代绍兴堕民群体世代为官妓,直至1904年才获准“改业从良”。
②强制征发制度
汉代“七科谪”将“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者家属充作官妓,记录于《史记·大宛列传》。
元代《通制条格》规定“犯罪妇女,除正妻外,余皆发付教坊司”。明代永乐帝将建文旧臣妻女“转营奸宿”,如铁铉妻女被“发付教坊司,昼夜二十余汉看守”,记录于《奉天刑赏录》。
③禁止赎身条款
宋代《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妓乐人不得与官员为婚,违者徒二年”,以此切断从良通路。
明代官妓赎身需官府发放“除籍帖”,但《南京刑部志》中记载,正统年间某官妓赎身被拒,理由是“恐开侥幸之门”。

管理体系中的强制服务
(1)轮值应差制度
唐代教坊妓女实行“旬休制”,《教坊记》中记载“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见”。但在实际执行中,白居易《琵琶行》揭露“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的连续劳役。
宋代州府设“妓乐籍”,按“上厅祗应”制度轮值官府宴会,临安府规定“妓女每旬赴点,三次不到者杖二十”,资料记录于《梦粱录》。
(2)限定服务对象
元代《至元新格》规定“诸官吏宿娼,杖六十七”,但官妓必须“应承过往使臣”。这种制度性虚伪,直接将官妓定位为权力附属品。
明代南京富乐院官妓“止容商贾出入”,官员需持“印信执照”方可召妓,这种制度实则形成了权色交易网络。

军妓管理体系
(1)军事化管理体制
汉代“营妓”由护军都尉直接管辖,在《居延汉简》中记载,戍卒“月食三石,妓给盐二升”,将妓女纳入军队后勤体系。
唐代边疆军镇设“营妓轮值簿”,敦煌文书P.3841号中记载,“沙州营妓每月需应差十五日”。
(2)战时特别管制
宋代《武经总要》中规定:“行军所至,择民间女子充营妓”,岳飞部将王贵曾因“强取民女为营妓”被弹劾,记录于《三朝北盟会编》。
清代对准噶尔作战时,年羹尧令“获番妇二百,分赏将士”,从而形成了临时军妓制度,记录于《圣武记》。

人身控制手段
①空间禁锢
唐代平康坊实行“坊墙制”,官妓出入需持“行牒”。宋代酒楼设“红灯区”,官妓“不得越界招客”记录于《东京梦华录》。
明代南京十六楼官妓集中居住,《金陵琐事》记载“每楼设官监视,夜锁院门”。
②经济枷锁
清代扬州养瘦马者“买雏女教歌舞,长则高价售之”,形成人口贩卖产业链,记录于《扬州画舫录》。
而且,妓院普遍实行“印子钱”制度,《清稗类钞》记载,上海妓女“负债满百金,则终身不能自赎”。
③暴力镇压
元代官妓逃亡按“逃奴律”处置,《元史·刑法志》规定:“娼妓逃亡,杖七十七,复役”。
明代锦衣卫设立“教坊司刑房”,正德年间有官妓因为拒侍,竟被“以铁帚刷其阴致死”,记录于《万历野获编》。
明代《刑科题本》记载,嘉靖三十七年,扬州官妓周氏因拒绝侍寝盐商,被鸨母“烙铁灼胸,伤重致死”。
在余怀《板桥杂记》中揭露,秦淮官妓“晨起即施脂粉,至夜分不得息,有病不许告假”。

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首次废除“乐户”制度;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禁娼令》。但这种延续千年的压迫制度的真正改变,是在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关于严禁妓院及妓女活动的决定》。
古代性服务者的血泪史,成为审视封建社会性别压迫的重要镜像。这种延续千年的历史存在,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矛盾。
在当代审视古代“女性经济产业”时,不应止于简单的道德评判,而需看到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机理与文化逻辑。